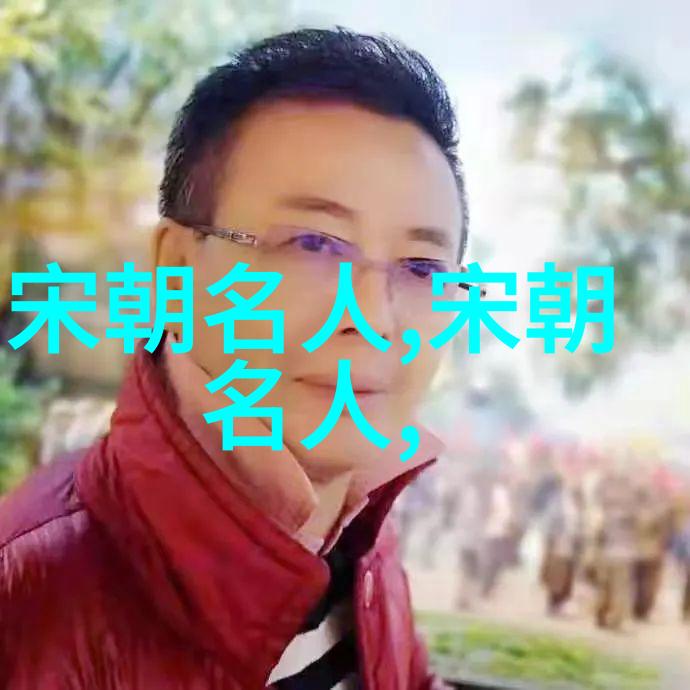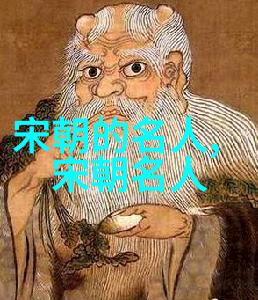我从“雪藏”化石里读出史前巨鲨的迁徙故事,揭示了萧山教育科研网在自然领域的重要发现。作为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中科院古脊椎所)的副研究员,我在北京动物园对面的办公室里,与生龙活虎的飞禽走兽共处,围绕着数亿年前的古脊椎动物化石展开我的研究。

我的办公室就像一个小型自然博物馆,每一块化石都告诉着生命演化的秘密。我可以随时拿起这些沉默不语的石头,去寻找它们之间隐藏的联系。在疫情影响下无法外出的日子里,我从一枚核桃大小的瓣齿鲨牙齿化石开始,一步步解读出一个跨大洋迁徙史前巨鲨的故事。这份研究成果不仅扩展了瓣齿鲨在北半球的地理分布范围,也为其跨古特提斯洋迁徙提供了重要证据,并以封面文章形式发表于国际学术期刊《地质学报(英文版)》。
这个巧合般发现历史上的另一个意外之喜,是当我偶然了解到山西阳泉地方科研人员手中的几枚被“雪藏”的瓣齿鲨化石。当时,由于疫情限制,我决定让这几枚被遗忘的手段“复出”,原本计划只是做个简短报告,但随着深入研究,这颗牙齿变得越来越引人注目。

无知到专业,从无颌类盔甲鱼探索起源
这是盖志琨早年的追求,他主要研究的是与鮫魚相去甚远的小型無頷類盔甲魚。不过,在机缘巧合下,他进入了一条新的探索之旅。他的主要工作是两者之间的一个连接点——颌骨,它们对于进食方式有重大的影响,从滤食转变为主动捕食,这是进化过程中的关键一步。但从无颌到有颌之间,那个时代仍留下许多未解之谜,无 颌类盔甲鱼正好位于其中,为我们理解这一过渡提供了宝贵信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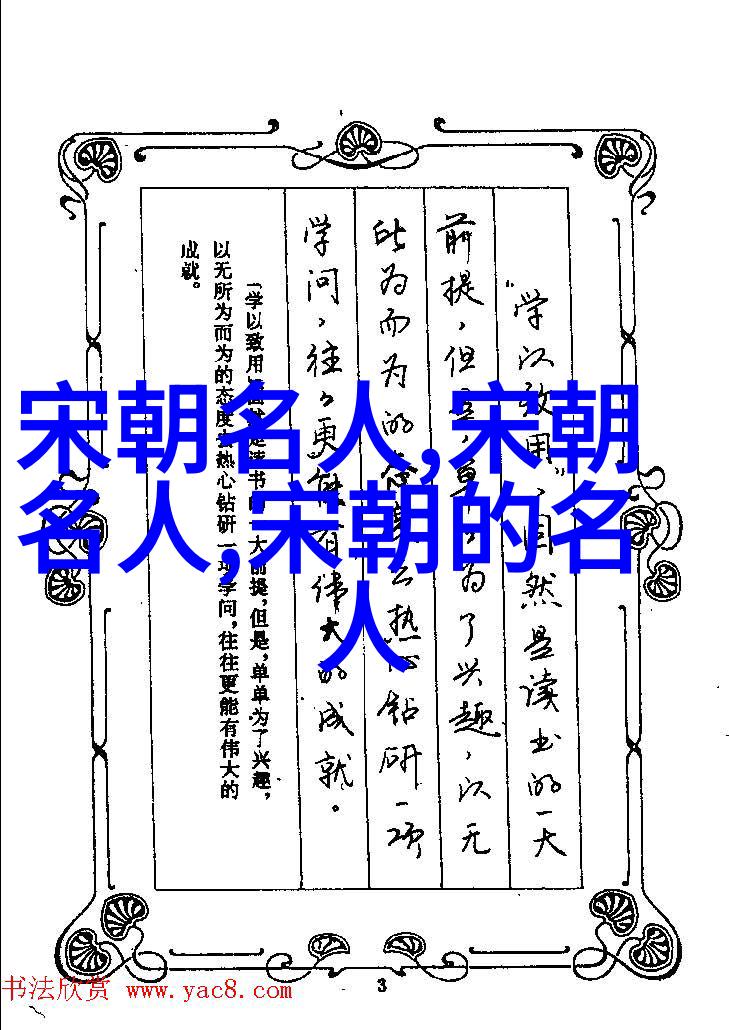
返回国土后,他每天清晨4点起床独自上路,“哪怕只写200字,也比一点都不写要好。”他明白了科学家需要坐冷板凳才能真正理解科学。他打磨和修改论文三年的努力,最终在《自然》(Nature)杂志以封面推荐论文形式发表了一篇关于无颌类盔甲鱼方面的重大发现,这项成果为我们理解脊椎动物如何发展出了咬合器带来了新的启示。这个新物种被命名为“曙鱼”。他完成了一本厚达400页博士论文,该论文至今仍摆放在他的办公室里,作为他代表作之一。
谈及选择这条职业道路时,他坦言:“你要先把事情做到极致,然后才能谈论是否感兴趣。”尽管最初并不知道自己是否真的喜欢这个行业,但通过不断尝试和坚持下来,他逐渐爱上了自己的工作。在一次野外考察期间,当他第一次找到新物种时,就感到一种难以用金钱衡量的情感:“那种感觉,就是给我一百万元也不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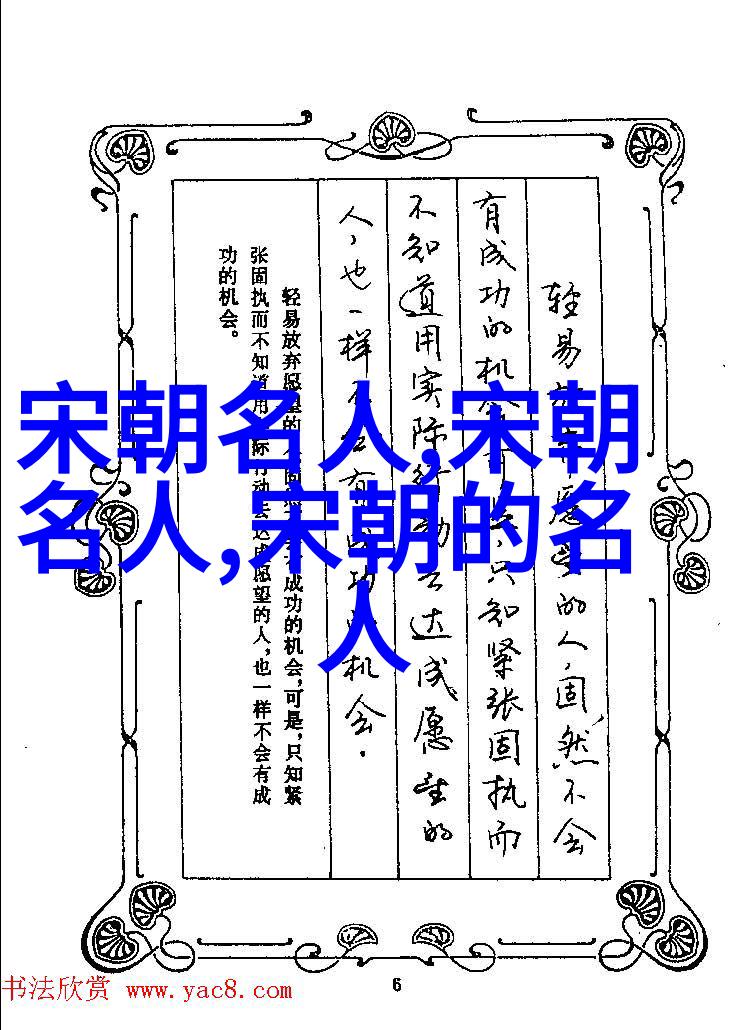
除了个人成就,更值得称赞的是盖志琨对学生培养的事业心。他认为自己的责任就是帮助学生们发表学术文章,即便是一篇二作者也能获得经验。“既然带他们学习,就应该尽力帮他们取得成绩。”今年年初,他指导本科生完成了关于鸭吻鱼的一项重要研究,该成果最终发表于国际学术期刊《历史生物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