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的家乡流行唱黄梅戏,他小时候是浸润在黄梅戏的音乐中长大的。1958年他凭借拉得一手好二胡,以独奏《良宵》考进了安徽省艺校,整整学了三年黄梅戏音乐,学会了作曲。他说自己对黄梅戏的熟悉程度和喜爱程度都远远超过了庐剧,当初他的同班4个人后来只剩下他一人,别人都不学了,他依然在坚守,立志要为黄梅戏艺术做出点成就。然而就在他毕业时准备大展宏图的时候,学校却撤销了庐剧专业。当时学西洋音乐的何合浓被分配去了庐剧团,而徐代泉被宣布留校从事教学。徐代泉很不理解,以为领导弄错了,他认为按理应该把他分到庐剧团去才对。但学校领导说出的理由却让他心服口服:“我们是要为庐剧留一个种子。”但这个种子却没有机会发芽、开花、结果。

省艺校直到1993年才招了一个庐剧班,这中间30多年徐代泉一直学无所用,没办法他只好下决心转向黄梅戏。但黄梅戏与庐剧音乐是根本不同的,为了尽早掌握这个剧种,徐代泉采取了一笨办法——与黄梅戏表演班的学生一起上唱腔课。老师上课时,他一面听,一面记谱。由于功夫下得大,他比十几岁的孩子学得还快,到后来艺校的黄梅戲教学曲目基本上都是由他来写。
这一行干起来是既苦且难的。苦是苦在熬人,难则难在从事戲曲音樂要學的事物太多了。而從事戲曲音樂的人卻往往免不了與清貧和寂寞為伍,那些情況正因如此,在學者中少而又少。在這樣的情形之下,也許有人會問:為什麼還要繼續?對於那些熱愛黃梅戲的人來說,這是一種無法言喻的心情,是對傳統藝術的一種敬仰。

徐代泉说自己一生做过三项工作,一是在教书室里传授知识给新一代,一是在作曲厅里创造出属于自己的作品,一是在研究室里探索更深层次的问题。他曾经担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歌舞团副团长,并且还是中国电视台首批编导之一,还参与制作了一系列关于古典文化的大型节目。此外,还有许多其他的事情,如撰写论文、参加讲座等等,都让他的生活充满活力和挑战。
不过,无论如何变化,都不能改变那份对黃梅戲音樂電視劇以及相關創作持續追求下去的心。这使我感到欣慰,因为這也是我最擅長的地方。我知道,這並不是容易的事情,但它是我生命中的重要部分,我願意為此付出一切。我想繼續下去,因為我認為這個世界需要更多美好的東西,而黃梅戲就是其中的一部分。在未来的日子裡,我會繼續創作,用我的方式來表達我的感受,用我的聲音來傳遞我的故事。如果你也喜歡黃梅戲,你一定會明白我們今天聚集在這裡,有什麼特別的事情正在發生。你們是否能感受到,就像我每天寫著寫著,不斷地尋找那份完美?

至于那些曾經想要离开或已经离开的人们,他们或许会问:为什么还要坚持下来?答案可能只有当你真正投入其中的时候才能体会,那是一种无法言说的感觉,它源自于内心深处,对艺术这种精神食粮的一种渴望和热爱。在那个过程中,即便遇到了困难和挑战,也能找到一种超越凡人的力量,让人忘掉身边所有烦恼,只专注于这段旅程本身。
当然,有时候这样的旅程并不平坦,有时候甚至感觉像是走火入魔一样,但是这正是艺术创造力的体现。那样的状态让我陶醉,每一次完成作品后的那种轻松愉悦,以及听着演员录音带回味再三时那种陶醉之情,这些都是我最珍贵的财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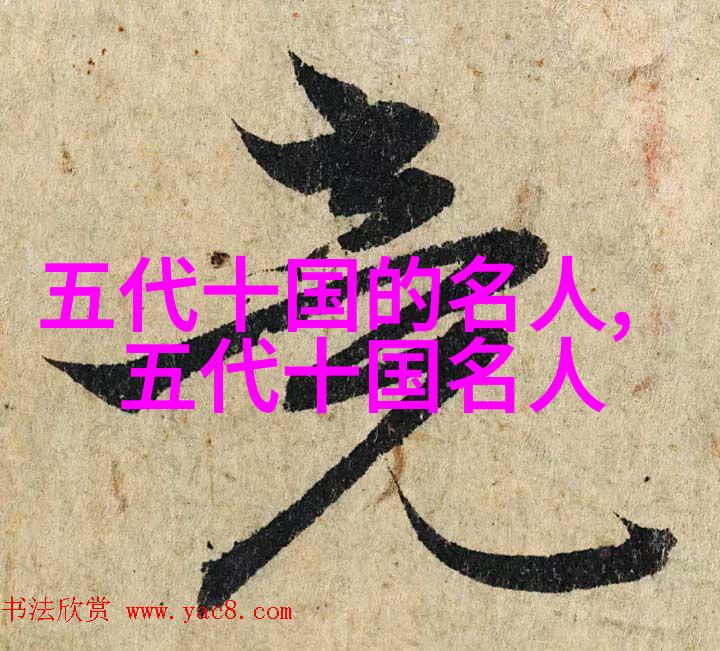
现在65岁高龄仍然保持着精力充沛的心态的是徐代泉先生。他以其卓越的地位,在中国乃至国际舞台上,为人们带来了无数欢乐和启示。他是一个传奇人物,从不停歇地追求着自己的梦想,同时也激励着无数追随者前行。在接下来的岁月里,无论风雨兼程还是顺风顺水,我们都将继续跟随着他的足迹,为这个世界贡献更多色彩,更丰富的情感,更真实的人文关怀。而对于我们这些幸运儿来说,即使只是简单地聆听或者观看这些经典唱段,也已足够成为我们生命中的宝贵财富,让我们共同沉浸于这片神奇而又温暖的地球,将我们的灵魂镌刻在历史的大画卷上。



